嘉陵江的雾又漫起来了,这座被称作“山城”的城市,在2022年的深秋,被另一种迷雾笼罩——那是全民核酸检测的队伍在晨雾中蜿蜒,是消毒水的气味在楼道间弥漫,是无数重庆人眼中难以消散的忧虑,我的手机屏幕亮起,母亲发来信息:“小区封了,你爸的药还够三天。”文字后面跟着一个微笑表情,那是她惯用的掩饰焦虑的方式,我盯着那行字,拇指悬在屏幕上方,却不知如何回复,疚,像一块被江水浸透的石头,沉甸甸地压在心口。
重庆的疚情,从来不只是病毒本身,它是一种复杂的情感结构,由距离、无奈与沉默共同构筑,我的邻居陈阿姨每天在阳台上敲击铁盆,不是为任何口号,而是让对面楼栋独居的老伴知道她还安好;外卖小哥小张连续二十天睡在站点的纸板上,不是为额外奖励,只为能继续给封闭小区送菜;我的表哥作为社区干部,凌晨三点还在核对流调信息,手机里存着女儿发来的视频:“爸爸,我学会唱《孤勇者》了”,他却抽不出三分钟回复,这些碎片共同拼贴出重庆抗疫时期的众生相——每个人都在用各自的方式对抗病毒,更在与内心深处的疚意角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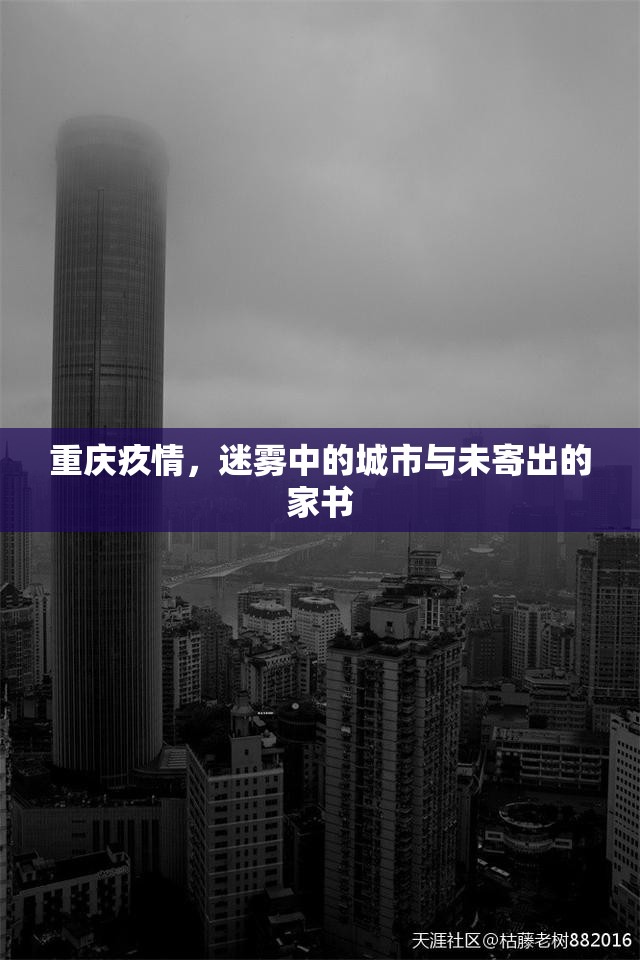
疚情中最锋利的部分,来自于对至亲之人的亏欠感,我的朋友林医生连续四十天未回家,四岁女儿通过视频哭着问:“妈妈不要我了吗?”她只能隔着屏幕亲吻孩子,转身又穿上防护服,我的大学同学被困上海,父亲在重庆手术却无法陪护,每天在异地健康码和重庆医院公众号之间来回切换,成为一种赎罪的仪式,这些故事没有惊天动地的悲壮,只有日常琐碎中的煎熬,正如心理学家所言,大规模公共卫生事件中,次级创伤不仅来自于对感染的恐惧,更来自于无法履行基本伦理责任带来的道德痛苦。
这座城市的记忆深处,疚情早已不是陌生客,抗战时期,重庆作为陪都承受了日机长达数年的战略轰炸,当时报纸上常见“未能保全亲人,深自愧疚”的启事;三线建设时期,无数家庭分隔千里,父母在给子女的信中写满歉疚;甚至更早的湖广填四川,移民们对故乡宗族始终怀有世代相传的负罪感,重庆的地形注定这里的人既要攀爬陡坡,也要背负情感的重担,如今的防疫疚情,不过是这种情感模式在新时代的延续与变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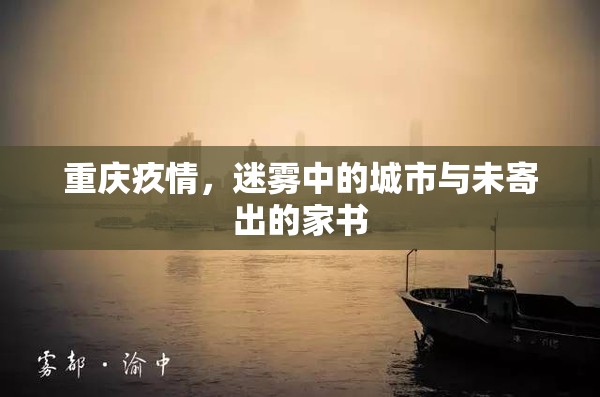
然而重庆人消化疚情的方式极具地域特色——用麻辣化解苦涩,用幽默消解沉重,微信群流传着段子:“以前是火锅选微辣中辣特辣,现在是核酸做一天两天三天”;志愿者大白背后写着“红码绿码,都是重庆码”;被封控的小区阳台上开起“个人演唱会”,有人弹吉他有人唱红岩魂,这种苦中作乐不是麻木,而是一种深刻的生存智慧:既然疚意无法避免,就让它成为连接彼此的纽带而非隔离的高墙。
解封后第一天,我回到父母家,父亲轻描淡写地说:“药够的,邻居帮忙买了。”母亲端出我最爱的辣子鸡,绝口不提封控时的艰难,我知道,有多少未曾言说的担忧被悄悄咽下,有多少疚意被刻意淡化,离渝多年的朋友发来消息:“看新闻说重庆解封了,真好。”我回复:“回来吃火锅吧,我请客。”——这是我们心照不宣的和解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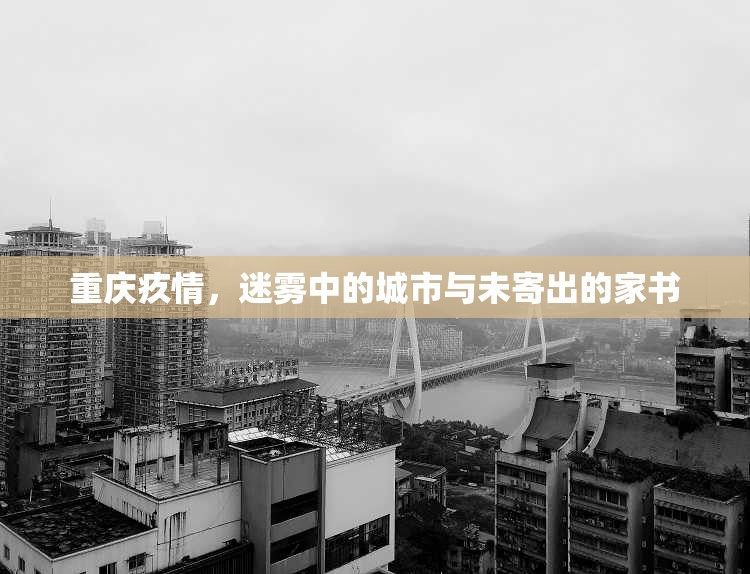
重庆的疚情终将随江水流去,但某些东西沉淀了下来:那些深夜闪烁的手机屏幕,阳台上的铁盆声响,志愿者防护服上的手绘笑脸,它们共同诉说着:疚意或许是爱的另一种形态,是联结断裂时的痛感,是重视彼此的证据,当两江交汇处的晚风吹散最后的迷雾,这座城市终将明白,克服疚情的不是遗忘,而是更深的理解与包容——对他人,也对自己。
本文来自作者[admin]投稿,不代表辫儿号立场,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bainet.com.cn/kepujiehuo/994.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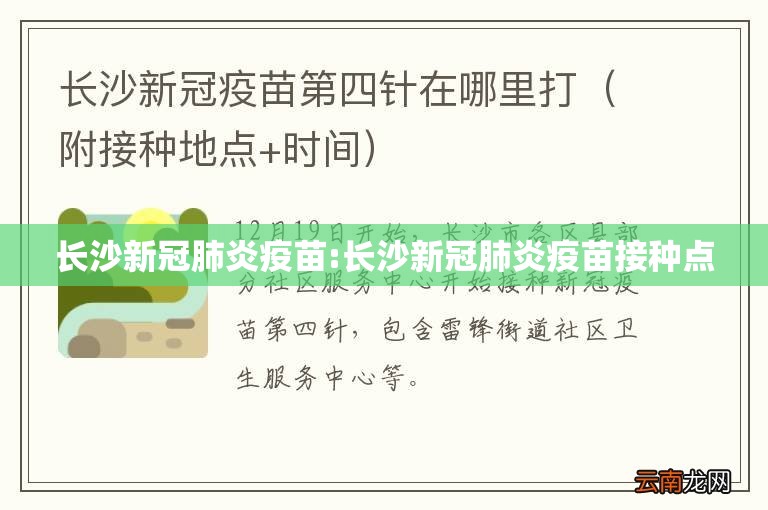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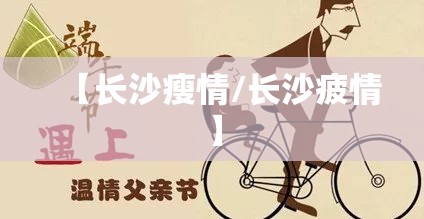



评论列表(4条)
我是辫儿号的签约作者"admin"!
希望本篇文章《重庆疚情,迷雾中的城市与未寄出的家书》能对你有所帮助!
本站[辫儿号]内容主要涵盖:
本文概览:随着国内疫情多点散发,许多市民和网友都在关注一个问题:“郑州封城了嘛?”这个问题不仅反映了公众对疫情动态的关切,也凸显了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信息透明和政策执行的重要性,本文将基于最新官方数据和政策,深入探讨郑州的疫情防控措施,分析是否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