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外滩的警戒线在四月风中猎猎作响,空荡街道回荡着消毒车的轰鸣,而八百公里外的安徽农村,深夜土路上颠簸的电动车灯光划破寂静——这束微光载着从隔离围栏缝隙逃回的打工者,奔向可能早已封锁的村庄,当媒体聚光灯聚焦国际化大都市的抢菜焦虑与方舱景观时,一场被刻意淡化的省籍人口大迁徙正撕开疫情管控的神话面纱,暴露了发展主义叙事下流动人口沦为系统性牺牲品的残酷真相。
安徽在上海的流动人口高达260万,他们构筑起都市运作的隐形骨架,却在危机时刻被排除在资源分配体系之外,当超市货架被中产社区的团购订单填满,不会操作智能手机的安徽保洁员正用最后的盐水煮面条;当网红晒出隔离期收到的奢侈品礼盒,建筑工地的皖籍工人正在板房里计算着剩多少泡面能撑到解封,这种资源获取能力的阶层分化与省籍身份高度重合,绝非偶然,而是城市治理长期将流动人口视为“暂住者”而非“权利主体”的制度性歧视的必然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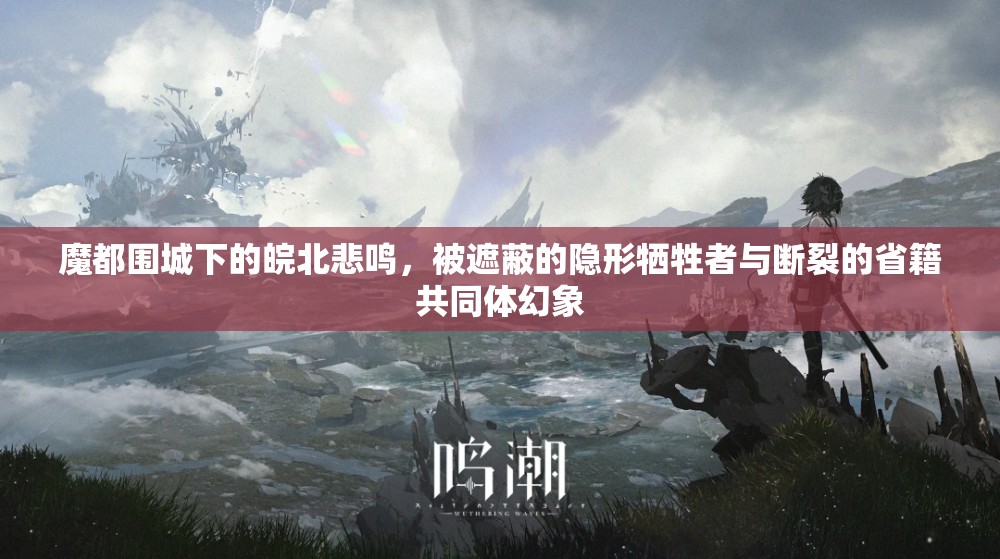
更为荒诞的是,地域污名化在疫情期间借尸还魂,某些小区业主群流传“安徽保姆带毒传播”的谣言,外卖平台出现“无安徽籍骑手”的隐形筛选,这种新时代的“地域防疫主义”将公共卫生问题扭曲为身份政治问题,仿佛给特定省籍贴上病毒标签,就能 magical 消除系统性防控漏洞,这种思维与百年前租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共享着同一种歧视逻辑,只不过披上了防疫科学的外衣。
当城市按下暂停键,农村被迫承担重启的成本,安徽村镇接收着从沿海城市折返的劳动力,这些地区医疗资源本就薄弱,如今更要应对可能出现的疫情输入和隔离压力,阜阳某村支书哭诉:“上海扔回来的人,我们要接住,可县里给的防护服只够用三天”,这种核心城市向边缘农村转移风险的行为,赤裸裸揭示了所谓“全国一盘棋”实质是“农村为城市兜底”的残酷棋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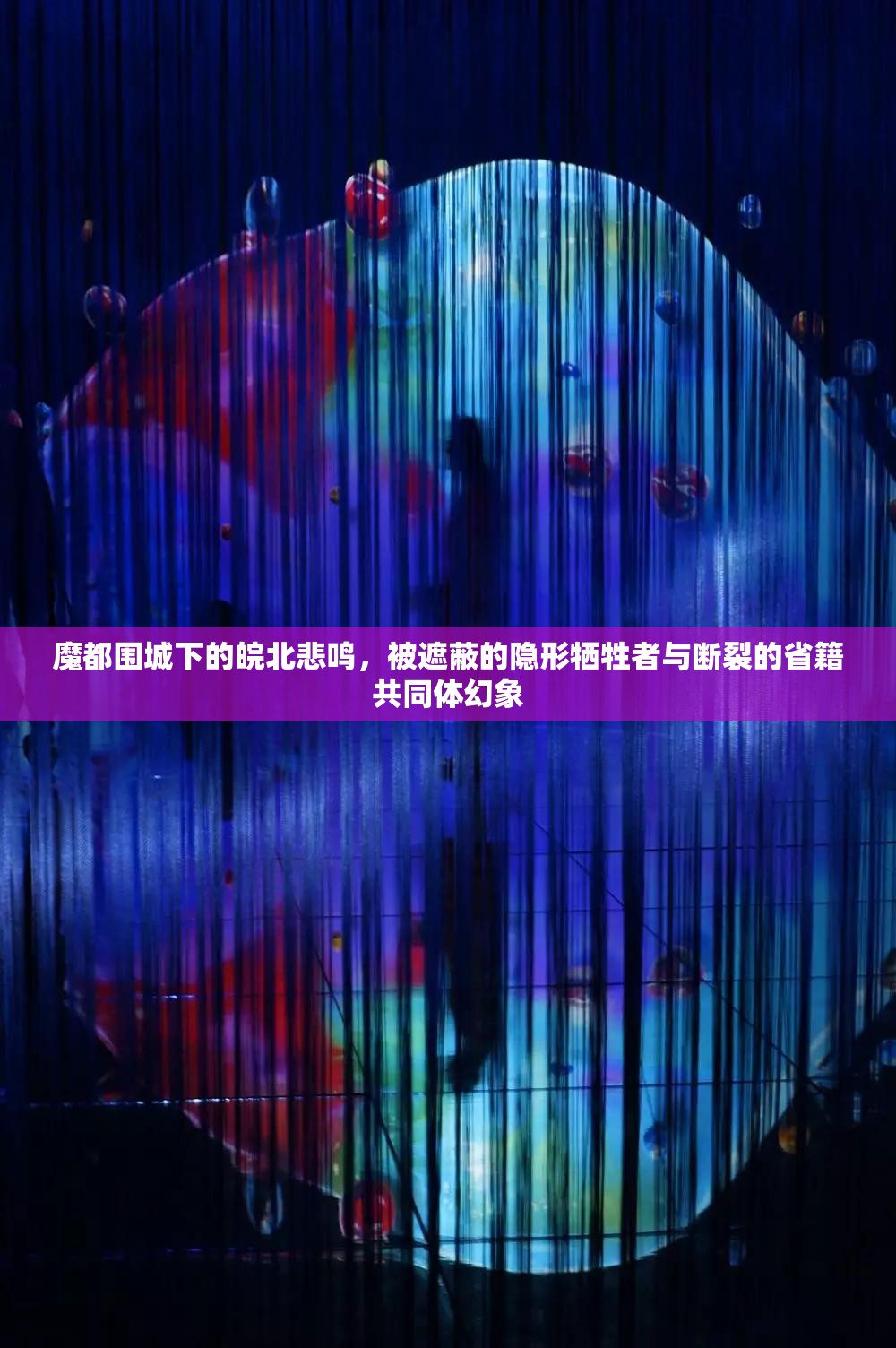
疫情应对成为检验社会包容的试金石,而结果令人心惊,流动人口在常态时期被诟病“挤占城市资源”,在非常时期却被要求“就地自我负责”,始终无法获得完整的公民身份认同,他们的困境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经济吸纳与社会排斥可以并行不悖,发展主义话语下的“命运共同体”,不过是既得利益群体编织的精致幻梦。
皖北田野的油菜花在春风中翻滚金色波浪,它们从不管根下的土地是富裕还是贫瘠,而那些被迫踏上归途的打工者,站在麦田边缘眺望远方沉默的铁轨,他们比谁都清楚——下一趟列车的方向,依然只能通往那座永远把他们当作临时零件而非血肉之躯的巨型城市,这场疫情终将作为统计数字存入档案,但地域割裂与阶层固化的基因突变,早已深植入社会肌体,等待下一次危机的激活,当城市霓虹再次照亮夜空,谁还记得那些被迫消失的背影,以及他们身后无数个陷入更深沉默的村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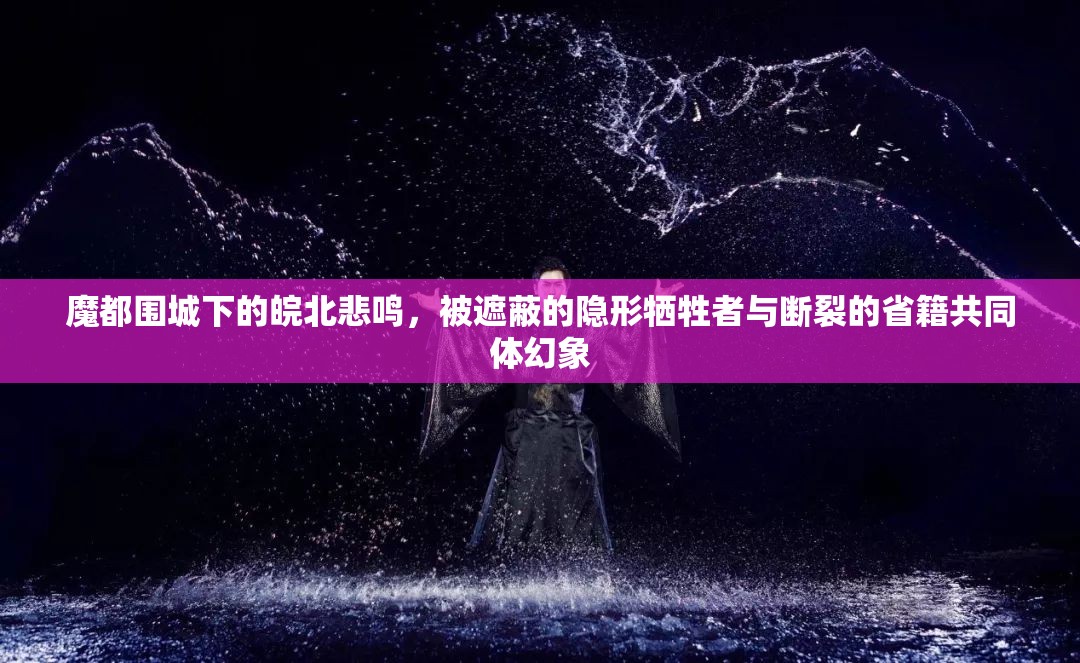
本文来自作者[admin]投稿,不代表辫儿号立场,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bainet.com.cn/shenghuojingyan/85.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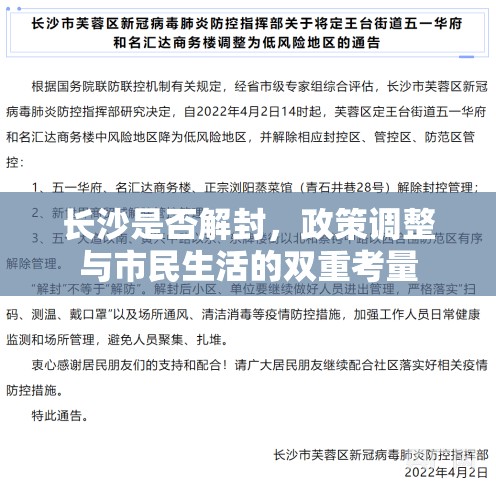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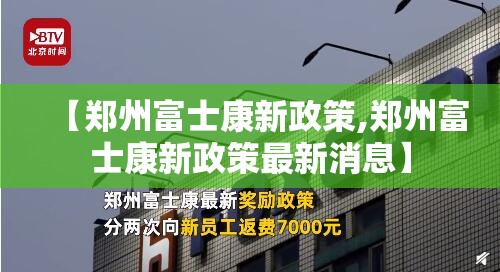

评论列表(4条)
我是辫儿号的签约作者"admin"!
希望本篇文章《魔都围城下的皖北悲鸣,被遮蔽的隐形牺牲者与断裂的省籍共同体幻象》能对你有所帮助!
本站[辫儿号]内容主要涵盖:
本文概览:郑州富士康科技集团(以下简称“富士康”)作为全球电子制造巨头的重要生产基地,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公司推出了一系列新政策,旨在优化生产环境、提升员工福利,并适应后疫情时代的产业变革,这些政策不仅反映了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承担,更凸显了中国制造...